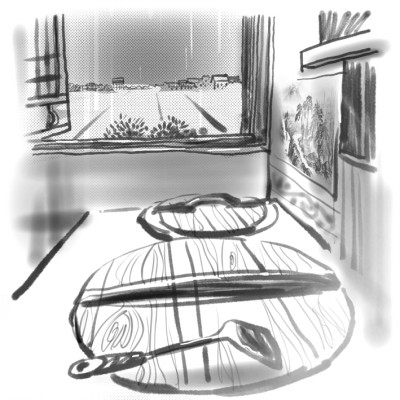
郭红松绘
“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站在小雪时节绿意依然的杭嘉湖平原上,我想起了陆龟蒙的这句诗。经历了连续的雨天和气温的骤降,大地即将进入休眠。
走在那片土地上,我时时忍不住微笑。此刻,当我回想、记录,又忍不住微笑。我愿意回想那些美好的画面,享受一份由衷的欢喜。
一
从木窗望出去,一大片金色稻田铺向远方,一阵浓郁的稻香瞬间逼近,漫至鼻尖。将目光收回,一个古老的灶头、灶头上同样古老的一幅幅彩画落入了视线。
雪白的底色,浓烈的色彩,画的是神话故事、历史人物、花鸟竹鱼,也有百姓劳作、生活的场景,勾勒的,是一屋、三餐、四季的回忆,传递的,是浙北水乡渔农文化和运河湿地文化交织的浓郁韵味。
“有家必有灶,有灶必有画”,嘉兴古塘村的乡土艺术,体现了生活的仪式感,也是对人生的慰藉。已过古稀之年的灶画艺人施顺观从18岁执笔至今,画过的灶头不计其数,收过的徒弟也不少,灶画艺术却濒临失传。让老人欣慰的是,去年夏天,30名小学生第一次在古塘村认识了灶头画,当场拜了师。
灶头窝着两口大铁锅,冒着热腾腾的香气。主人揭开靠窗的锅,炖了几个小时的红烧鹅嘟嘟沸滚着,揭开另一口锅,细密的竹篱笆片托着一大块用稻草系着的红烧肉,已炖得酥烂,油光锃亮,热气腾腾,令人垂涎欲滴。
“晚饭马上好了。”他砰地盖上锅盖。
我将冻得冰冷的双手伸向灶里的柴火,柴火即将熄灭,微微的星火一呼一吸,像在说,屋后有田,锅里有肉,别急别急。
等晚饭的时候,我站在桥边看一群鸭子游水,一群鸡在水边的篱笆墙边喊加油,有几只飞上了结满红果的柿子树,伸长着脖子,一只小黑狗冲鸭子叫两声,又冲鸡们叫几声。我站在桥上看热闹,呵呵笑。桥的另一边,一个农妇在岸边锄地。我远远地看着她,想,村里的农耕文化馆里,是否有她家捐的农具?绣娘工作室里,可有她的绣品?某个周末,会有一群城里来的孩子到她的田里跟她做农事吗?她顾自锄地,顾自接手机来电。我又想,她家里一定也用上了煤气灶、抽水马桶,临睡前也会刷抖音,冷了也会开空调,过节了也会网购,她走的夜路,每一步都有路灯照亮。
稻草肉和红烧鹅太好吃了。嘉兴禾帮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土”,土得活色生香。此时此刻,应了离此不远的海宁徐志摩故居里的一句话:“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份,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二
画了30多年画的农民画家美宝站在油车港菱珑湾小巷入口的廊檐下,仰头看着脚手架上画着墙画的三个兄弟。零星的微雨飘过,打湿了她掺杂了几丝白发的短发和近视眼镜。已经画了三天,要将整面墙画满。都是喜庆的题材,鲤鱼跳龙门、赛龙舟、粮仓、桃树。
千百年来,源于逢年过节、衣食住行、生丧嫁娶等民俗,汲取了传统剪纸等民间艺术的嘉兴农民画成了江南水乡的一朵奇葩。上世纪80年代起,20岁左右的美宝们便开始涂鸦。这是一群从田埂上赤脚走来的农民,他们白天下地,夜晚作画,用最稚拙的笔法、最农民的审美、最无拘无束的想象、最真挚的乡情,把密布的河网、清澈的水流,把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桑绿稻黄、蚕肥鸭壮、古芳流韵和自己的生活都画在了房子里、围墙上、灶头上以及画布和白纸上。承载着中国乡村几十年巨变的一幅幅农民画,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记忆、一卷史诗。
在农民画馆里,我见到了“油车港十姐妹”的画——是12位农村老太太,最大的快八十了,最小的快六十了。画的大多是劳动的场景,采桑、捕鱼、晒谷、收粮、车水、插秧等。有几幅印象派风格的,是她们的老师缪惠新的画,他的画已在十几个国家展出,登上过《时代周刊》。
美宝的《月夜》画的是一个老人抽着烟斗,长满菱角的湖水里张着网捕鱼,一弯月和一只狗陪着他;《新丝绵上市》画的是女人孩子们围着一个水缸剥蚕茧套丝绵兜,身边是鸡鸭猫狗们,每个人每只动物都憨态可掬,让人一看就不由自主地微笑。
美宝和这些老太太的画都曾在全国美展展出,并远渡重洋去澳大利亚等多国展出,她们仿佛也随着画,走到了很远的地方。
三
风很大,很冷,我绕着那棵巨大的、棕红色的“稻穗”走了一圈,感觉到了暖意。
这座造型奇特的建筑是运河畔陶家村旧粮仓改造成的网红空间——陶仓理想村。几个月前,十多场艺术活动吸引了长三角上万游客来此打卡。嘉兴这座建制于秦朝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繁华富庶,名人辈出。陶仓,曾是明清时期王江泾名门望族陶氏宅居所在地,后被征作粮站、植绒厂,闲置时经历了一场大火,废弃多年。一群年轻的“80后”保留了粮仓主体和红砖元素,将它变成一个三千多平方米的艺术中心,像高耸入云的一棵稻穗。中庭,一束天光漏下来,对比并不强烈的光影给人无限的想象。东仓和西仓,黑色铁质旋梯与砖红墙面,水磨石荷花图案地面,巨大的拱形落地玻璃窗,玻璃窗外层层叠叠的拱形连廊,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进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错觉。
颜值只是陶仓的一个元素,这里定期举办的艺术活动如“新陈代谢”当代艺术展、植物装置艺术展、新车发布会、创意市集、迪斯科舞会等,吸引了远方的年轻人和近处的居民,读诗、弹唱、烧烤、吹风、遛弯、看露天电影、住帐篷、看星星。
陶仓对面的一幢小白楼里,住着十来个工作坊的年轻“村民”,大多做文创和艺术,彼此间已亲如家人。这里,高度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理念和审美方式,他们将这里营造成了人与天地对话的乐土,人们最容易抵达的“诗和远方”。
就这样迎风走着,忘了是哪一个村庄,初冬的灰暗底色上,骤然亮起一片新绿,水边一畦畦萝卜芹菜莴笋如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围在老人身边。这个村庄已经很像一个城市了,甚至有花园,如果有一大片草坪就更像了。好在没有。村里将本该做草坪的地分给了家家户户用来种菜,围上了篱笆。乡村空间的重塑,不是简单模仿城市,而是与乡村风貌契合,菜地和村庄才是绝配,就像我走进一户农家,听到鹅齐声叫唤,随后听到一位老人问我“饭吃过了吗”,而不是“你好”。
四
卖爆米花的中年人悠闲地坐在桥边的一条石凳上,炉子自动旋转着,香味随风弥漫了小雪时节的梅花洲。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伍胥山头花满林,石佛寺下水深深。”千年石佛寺静静伫立,两棵千年银杏隔水遥望,满地金黄的落叶让我想起秀水新区的银杏天鹅湖。天鹅湖边刚栽下了一大片银杏林,像正在发育的少年,散落其中的小火车站、咖啡吧文艺范十足。我想象着这些树长大后的样子,眼前浮现了一大片和阳光般纯粹坚挺的金黄。
又想起一个村庄,进去才明白,是个村子,也是个动植物园,有猴子、天鹅、梅花鹿、羊驼,还有浮在水上一动不动以假乱真的野鸭,真是煞费苦心——我忍不住笑了,一边想,日日生活在这里的人该多么欢喜。
四十年前,父亲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在绿水青山间长大,将家从镇上搬到了村里。然而,门前通往小镇的小路,一下雨全是泥泞,邻居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咸菜就番薯丝汤。一次,父亲下班回家见两个纤弱的女儿正从村口大水井打满一桶水吃力地抬回家,突然觉得心疼,他心目中“乡村乐园”的概念里没有这一幕,无数人对“诗和远方”的向往里,也没有这一幕。
四十年过去了,某个夜晚,父亲给我发来微信,说娘家小院通往小镇菜场这最后一条泥路也浇上了柏油。
走在任何一个被现代化改头换面的村庄,我不会一味怀念从前的乡村,谁都有把日子过得更舒坦的权利,谁都不能想象所有农村人都待在村里哪儿也不去,炊烟袅袅地等着你来拍照,我们也不愿看见村子里只剩下老人。
村庄像一位老人,他的目光是黄昏时分村口亮起的灯,灯照见大地上无数个村口,一些年轻人的脚印伸向村外,一些年轻人的脚印伸向村里。行色匆匆的人们在无数个村口擦肩而过,每一个人都在用力生活用力爱。
小雪后,大地即将休眠,进入属于它的梦境,而后,又一次迎来春雨的浇灌。(苏沧桑)
